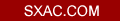"当时周总理胳膊受了伤,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他去苏联治疗,而我父亲也有严重的胃病,决定一同去治疗,就这样把我带去了。后来,我被送到了国际儿童院,并开始了我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。"陈祖涛回忆到,"当时国际儿童院大概有两三百人,别的国家都是一个、两个,我们中国的小孩则占到了十分之一,其中,包括主席的大儿子、二儿子、女儿,朱德的女儿以及刘少奇的儿子等等。"
当时被送去国际儿童院的是当时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弟,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里,也许这样才是保护好共产党领导人下一代的最好方式。
这些不同年纪、不同国籍、不同背景的孩子,他们聚在了一起。他们幸运吗?他们远离战火硝烟,他们远离了饥饿难耐,但也远离了故乡、远离了祖国、远离了至亲,独自成长。他们少年时的经历,给他们的一生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特殊印记。
虽然陈祖涛到苏联的时候还很年幼,但是他一边适应着环境,一边努力奋发。一晃过去了十多年,最终,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苏联著名的鲍曼工学院。到现在为止,陈祖涛还说,"我的俄文基础就是在那些年打好的,以至于后来,说汉语还不如说俄语流利。"
起步,60年的汽车生涯
从1945年开始,陈祖涛在鲍曼工学院学习机床与工具专业,也是在那个时候,他真正接触到了汽车行业。
那个时候,陈祖涛接触的都是苏联的汽车产业,为中国造车这个理想曾经也不止一次的出现在他的生命里,可是最后还是如雾般消散。因为那时的中国没有能力,而这个理想,也就成为了他心中深深埋藏的一条湍急河流,无法泅渡,那河流的声音,却每日每夜绝望的歌唱。
直到1949年12月,斯大林70大寿,全世界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到莫斯科来祝贺。当时毛主席也去了,他除了带去寿礼和祝福外,还想带回些什么,想从苏联为中国带回些什么。
这是中国领导人和斯大林谈苏联援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--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的谈判。
为了这156个援建项目,中国派了一个以总理为首的庞大代表团,包括工业的机械工业、冶金,包括军事的航空、坦克、飞机,当然,也包括汽车。现在的长春一汽汽车厂,就是当时的援建项目之一。

1951年陈祖涛在苏联大学毕业
凭借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俄文底子,陈祖涛参与了后来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的谈判。陈祖涛说,当时中国的俄文翻译屈指可数,除了主席和总理,到中层这一级,几乎没有翻译,所以机械组通过使馆找翻译,就找到了他。
"由于作为临时翻译,参与了一些与机械工业相关的谈判,包括一汽的整个谈判过程。所以我深深记得,苏联当时对我们,真的是无私的帮助,中国的工业基础,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苏联。"这位迟暮的老人在讲到这里时,神情有些闪烁,也许这些年来的我们与苏联的政治纷争让他有些耿耿于怀,因为那些曾经的帮助,在他的记忆中总是汨汨而过,温暖如同泉水一样涌出来,即便,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。
陈祖涛回忆到,"在这过程中,也结识了以沈鸿为首的我国机械工业的创始人。沈鸿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业专家,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毅然放弃在上海的产业,带着部分机器设备,辗转来到延安,成为我党第一代兵工专家。沈鸿告诉我,建汽车厂是斯大林亲自向毛主席提出来的。斯大林说,汽车厂代表现代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,你们建一个汽车厂,就可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和钢铁、化工、建筑等其他行业向前发展。毛主席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。中国汽车工业便在苏联的扶持下,正式起步了。"
这时是1950年,也是他真正参加到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建设中的时间,而在1951年年初,急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他,便正式大学业回国了。
奠基,让一汽从无到有
对于陈祖涛来说,总理对他总是有如父亲般的关怀,他们之间,也有着一些情感的牵绊。有人说,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,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,忘记了他的笑容,忘记了他的脸,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,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
陈祖涛回忆起了回国初期和总理的那次谈话:"1951年的夏天,我见到了周总理,和我一起的,还有和我一同回国的同学赵施格。总理说,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?我们表示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。总理很高兴,问我们,你们学什么专业的?赵施格说,是冶金学院毕业学钢铁的,我想搞钢铁。总理说,那好,鞍钢正在恢复建设,你就到鞍钢去吧。我则说,我是学机械的,我在苏联的主攻方向是汽车。总理说,那好极了,你再回苏联去,其中汽车筹备组正在苏联谈判,你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谈判。就这样,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,我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第一名职工,从此开始了我为之奋斗终生的汽车事业。"